
「Ave Mujica」:循此苦旅,终抵群星?- 文本细读 - 第 1 集
从今天已通览全篇的上帝视角回顾,逐集细读「Ave Mujica」实在是一项堪比考古的精细繁杂工程——不仅因为它背负着前作「MyGO」13 集的叙事惯性与情感债务,更因为「Mujica」那刻意的、几乎是挑衅式的碎片化叙事本就拒绝给出一条稳定的阐释路径。如何从错综复杂的线索脉络中厘清具体每集的作用与意义,又应当从何处、如何切入,实在是一项难题。不妨我们就仿照 Reaction 视频的形式,看一段评论一段。也许这也暗合了伊瑟尔所述的「时间流」式的阅读过程,作品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推进动态地生长出来,每个新句段也会重排之前的理解、更新未来的期待。
「Sub rosa.」——「秘密」
先从标题开始吧。
拉丁语「Sub rosa」意为「在玫瑰之下」,源自古罗马时代的秘密会议传统,与会者会在会场悬挂玫瑰以示所言不得外传。那么问题来了,这一集是在守护什么秘密?表面上看似乎是指 Ave Mujica 成员演出时所佩戴的面具遮掩着她们的真实身份,但当本集若麦强行揭下所有人的面具时,你会意识到真正的秘密并不在于被揭露的面孔,而隐藏在更深的层面——隐藏在每位角色的内心深处。
01:10

开幕就不得不提及一个意象:月亮。为什么是月亮?
月亮:赋形、缺位、赦免
首先自然是源自作品本身的世界观设定:月光唤醒了人偶,使人偶获得了短暂的生命。第 1 集以月光开启全篇,也即把「月光 = 赋形 / 赋魂」的世界观母题摆在台面上。月光作为一种冷色顶光 / 背光,在黑暗中轮廓化的效果尤为明显。而同时我们知道,月亮的光并不来自自身,而是一种反射,这又使它天然带有「二次 / 衍生」的性质。月光下的人偶也即暗指主体并非天然完整,而是被某种外在的、舞台性的光照所塑形。人不是先有了「自我」再上舞台,而是在「被看见 / 被照亮」的过程中获得了形与名。这是整部作品人物塑造的总基调。
然后我们便会很自然地联想到,那为什么不是太阳?太阳去哪里了?
如果说太阳象征着秩序、裁决、律法——一种自上而下的、稳定的、父权式的规训力量,那么在「Mujica」的世界里,这个太阳从一开始就是缺席的。在之后的情节中我们尤其容易注意到,成年人的系统性缺位是贯穿整部作品的叙事底色。祥子的父亲清告本该是为女儿提供庇护的成年男性,结果却整日酗酒、瘫软在地,需要未成年的女儿来收拾残局。父亲不仅无法履行保护者的角色,反而成了需要被保护、安抚、照顾的对象,这种父职的倒置意味着象征秩序的根基从一开始就已经坍塌。类似地,睦的母亲无力察觉女儿内心的分裂与痛苦,反而通过种种行为进一步加剧她的崩溃;祥子的祖父在祥子最需要支持的时候也全然不在场,等他出现时也不过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与脸面,而非对孙女状况的真正关心。成年人要么缺席,要么不作为,要么只顾自身利益。无论哪种情况,结果都是一样的:少女们被抛入了一个没有太阳照耀的世界,只能在月光下自我照明、顾影自怜。
这就是为什么第 1 集的开场不是白日下的舞台,而是月光下的人偶剧场。月光不提供秩序与裁决,它只提供一种温凉而脆弱的「抱持性环境」——借用温尼科特的术语,这是一种母性的、非评判的、允许主体暂时栖身的心理空间。舞台在此成为梦境与避难所的混合体:它不解决问题,只是将问题延迟;它不给出答案,只是让提问者可以暂时不必面对那个无法回答的追问——「我该如何在一个没有成年人庇护的世界里生存下去?」
此外,太阳式的裁决还要求彻底的暴露与清算:罪行必须被揭穿,真相必须大白于天下。而月光则不是这样运作的,月光容许秘密的存在,不要求完全的坦白,不强求伤口必须揭开给所有人展示。在第 1 集中,尽管面具被撕下,但面具下的人依然在守护着更深的秘密(无论是祥子的家庭还是初华的身世)。你不必把一切都暴露在阳光下接受审判,你可以选择保留那些不愿示人的部分——月光赦免这样的行为。这也是为什么 Ave Mujica 的舞台必须在月光下而非阳光下展开。阳光会照亮一切,包括那些不愿被看见的伤疤;而月光只照亮轮廓,给予主体选择性暴露的自由。在这里,真相不必完全暴露,伤口无需彻底愈合,主体也不必须「积极向上、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这里不存在太阳式的道德说教。月光只是温柔地照亮破碎的、被遗弃的人偶,允许她们在不完美、不诚实、不健康的状态下继续存在,为她们提供一个栖身之所。这也正是 Ave Mujica 世界的核心旨趣,在之后的观影过程中还请记得:这绝非一个「太阳下的故事」。
01:12 - 04:24
KiLLKi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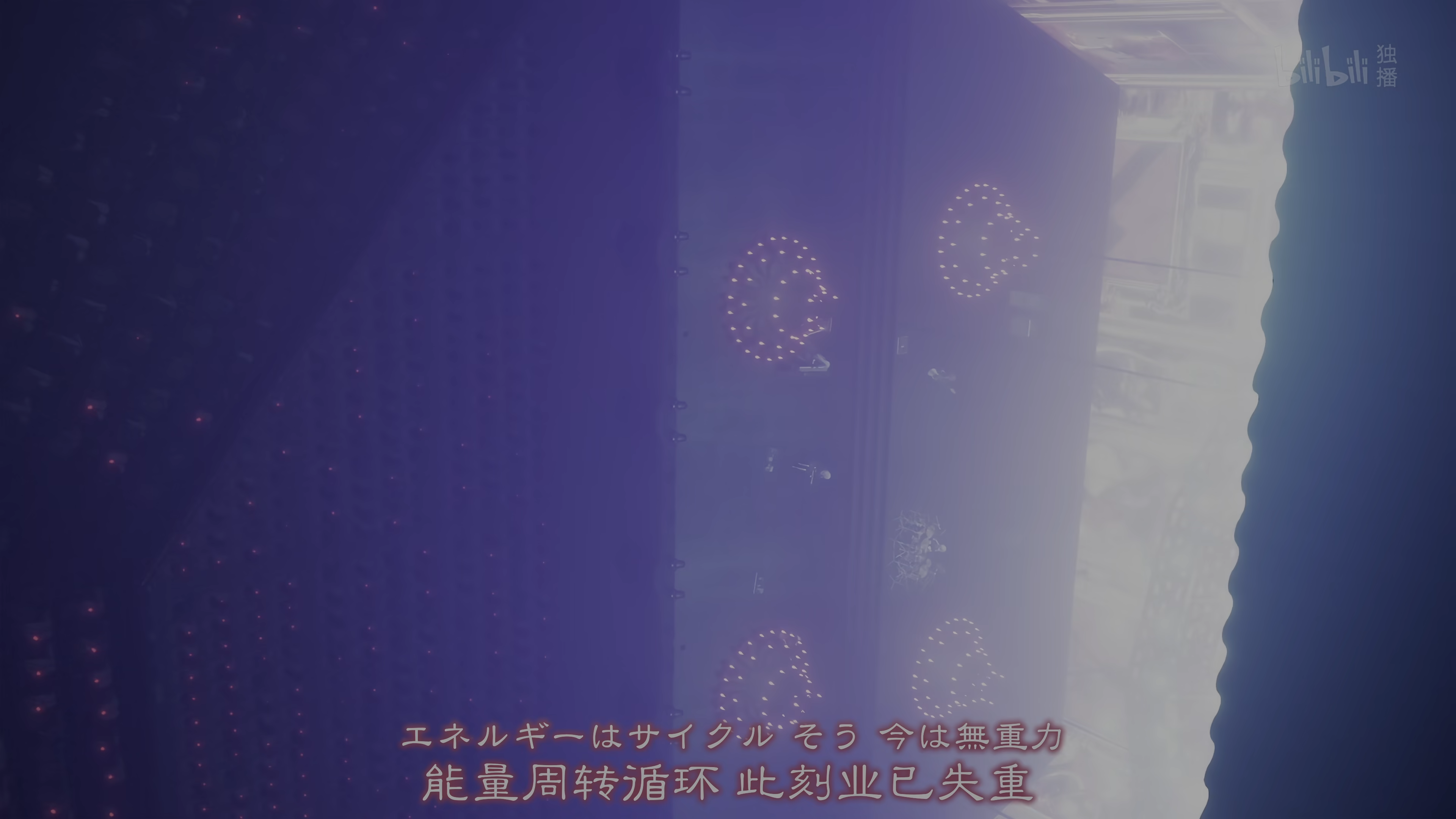
弄られて垂れ流す 音のない音
在命运玩弄下发出无声之音
遍く 名前を捨てたのね あなたのモザイクが泣いてる
将名字尽数舍弃 模糊的你哭泣着
can not, can not, not, not, not deny 紛れもなく真実
can not, can not, not, not, not deny 不折不扣的真相
さあ 預けて 回帰するように
请你托付于我 就此归来
エネルギーはサイクル そう 今は無重力
能量循环往复 此刻已然失重
象徴的なパレード この月夜に仰げよ仰げ
象征性的游行 举目仰望月夜
‘completeness’
「完好无缺」
嗚呼 命の灯を掲げ
啊 高举生命之灯
KiLLKiSS judy.., KiLLKiSS jude.., KiLLKiSS juda..,
KiLLKiSS judy.., KiLLKiSS jude.., KiLLKiSS juda..,
欺いて
瞒天过海
KiLLKiSS judy.., KiLLKiSS jude.., KiLLKiSS juda..,
KiLLKiSS judy.., KiLLKiSS jude.., KiLLKiSS juda..,
抱きしめて
紧抱入怀
ねぇ 無防備だね 美しい戯れに 人は壊れてゆく
真是毫无防备啊 甜美嬉戏令人毁于一旦
可笑しいわね
多么可笑
‘cuz we’re all alone
‘cuz we’re all alone
噛み締めても まだ痛むなら
倘若细品仍旧疼痛
手を挙げ 希え
高举双手 虔诚祈愿
oh, when you bleed, 惑星に そう その影を伸ばせ
oh, when you bleed, 在行星上投下阴影
ねぇ 私の世界(ほし)が知りたがっているわ さあ
我的世界正渴望知晓
you bleed, yes, bleed その血で 天(そら)の五線譜を書き換えれば
you bleed, yes, bleed 你的血液 若能改画为天空的五线谱
code ‘KiLLKiSS’ uh..,
code ‘KiLLKiSS’ uh..,
KiLLKiSS judy.., KiLLKiSS jude.., KiLLKiSS juda..,
KiLLKiSS judy.., KiLLKiSS jude.., KiLLKiSS juda..,
欺いて
瞒天过海
KiLLKiSS judy.., KiLLKiSS jude.., KiLLKiSS juda..,
KiLLKiSS judy.., KiLLKiSS jude.., KiLLKiSS juda..,
抱きしめて
紧抱入怀
ねぇ あからさまね 醜い終局に すべてが変わってゆく
真是明目张胆啊 丑陋结局将会改变一切
儚いのね
多么缥缈
そう このまま 壊れて
就这样毁坏吧
这运镜看爽了,估计制作组也做爽了,武士道在舞台演出方面无疑已积累起相当丰富的经验。无论是手绘还是现实中的镜头,恐怕都很难做到如此自由、随心所欲的运镜,可以说充分发挥了 3D 动画的优势——这也正是在影像方面我最看重的要素,即如何充分发挥这个媒介的独特优势。想当年看「LoveLive」的时候,那 3D 只能说不忍直视,如今的技术进步还是有目共睹。
OP 在整部作品中时常会起到全作线索、甚至说「全作剧透」的作用,以一种诗意的、隐晦的方式暗示了作品主题或角色命运,「KiLLKiSS」也毫不意外地成为了全篇的预言。
开场第一句就摆出了一种被动的姿态:「弄られて垂れ流す 音のない音」——在命运玩弄下发出无声之音。声音本该是有声的,但这里发出的却是「听不见的声音」,就像人偶被月光照亮后获得了意识,却无法真正言说自己的处境。
紧接着「遍く 名前を捨てたのね あなたのモザイクが泣いてる」——将名字尽数舍弃,模糊(马赛克 / Mosaic)的你哭泣着。不只是舍弃一个名字,而是「尽数」舍弃,意味着不仅是舞台上的假名 / 代号,也包括本名 / 艺名等一切标识的全面丧失。「马赛克」一方面指代了像素化的遮挡手段,在表象的遮蔽之下、真实的「你」变得模糊、无法辨认;一方面又指代了镶嵌艺术、即由无数碎片拼凑而成的图像,暗指「你」是由无数碎片(多重身份、多重面具)拼凑而成,在舍弃了名字之后,这些碎片便失去了作为一个统一主体的粘合剂,于是开始松动、分裂到无法辨识。马赛克本该是死物,但这里它却在「哭泣」,因为月光让人偶活了过来,获得了情感。此时哭泣的并不是那个表面的、统一的「你」,而是那些被遮蔽、被拼凑的碎片。至于「你」是谁?既可以是角色之间互相的对话,也可以是一种与自我的对话,也可以是面向台下的观众。实际上,这里的「你」可以指代一切名为「人」的主体。
这句歌词还挺值得玩味的,因为它其实同时暗含了两种视角:现象学(遮蔽)和解构主义(碎片)。
现象学 (Phenomenology) 作为 20 世纪最重要的哲学运动之一,其核心诉求可以用胡塞尔的口号来概括:「回到事物本身!」(Zu den Sachen selbst!) 这句话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对整个西方哲学传统的激进质疑。
1. 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悬置一切预设
现代现象学的奠基人埃德蒙德 · 胡塞尔 (Edmund Husserl) 认为,传统哲学和科学在认识事物时,总是带着各种未经审查的预设、理论框架和「自然态度」。我们从不直接面对事物本身,而是透过层层概念的滤镜来看待世界。
为了真正「回到事物本身」,胡塞尔提出了「现象学还原」(Phenomenological Reduction) 或「加括号」(Epoché) 的方法:
- 悬置自然态度:暂时搁置我们关于外部世界「客观存在」的一切信念。不是否定它们,而是把它们「加上括号」,不让它们干扰我们对现象本身的直观。
- 回到纯粹意识:将注意力转向意识活动本身——事物是「如何」向我们显现的,我们的意识是「如何」构造这些显现的。
- 本质直观:通过这种还原,我们可以把握到事物的「本质」(Eidos),即那些使事物之所以为事物的不变结构。
胡塞尔相信,通过现象学还原,我们能够抵达一个纯粹的、无预设的、绝对确定的认识基础。然而,这个乐观的信念在海德格尔那里遭遇了根本性的挑战。
2. 海德格尔的真理观:Aletheia——解蔽与遮蔽的共属
马丁 · 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gger) 继承了现象学的方法,但将其推向了更为激进的方向。他追问的不再是「意识如何认识对象」,而是更为根本的存在论问题:「存在本身是什么?」
海德格尔对古希腊语「真理」一词——aletheia (ἀλήθεια) 的词源学考察,成为其哲学的关键突破。Aletheia 由否定前缀 a- 和词根 lethe(遮蔽、隐藏、遗忘)构成,其字面意思是「去蔽」(Un-concealment) 或「解蔽」。这意味着:
- 真理不是符合论:真理不是命题与事实的「符合」或「正确性」,而是存在者从遮蔽状态中「涌现出来」、「敞开自身」的动态事件。
- 显现即遮蔽:关键的是,海德格尔强调,任何「解蔽」都必然同时伴随着新的「遮蔽」。就像手电筒的光束照亮了一个区域,却同时让周围陷入更深的黑暗。当我们以某种方式理解一个事物时,我们也就遮蔽了它的其他可能性。
- 真理的有限性:因此,「真理」不再是一个可以被一劳永逸地占有的绝对知识,而是一个永远处于张力之中的、动态的、有限的过程。每一次「显现」都是对无限丰富之存在的一次「截取」,必然遗漏、压抑、遮蔽了其他维度。
3. 现象学还原的悖论:名字的不可或缺性
当我们将海德格尔的洞察反向应用于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时,一个深刻的悖论就浮现出来:如果我们试图通过「悬置」一切概念、语言、名字来抵达「事物本身」,我们真的能成功吗?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
- 我们总是已经在语言之中:人类的意识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前语言的直观能力。我们对世界的体验从一开始就被语言所结构化。当婴儿学会说「妈妈」这个词时,他不仅仅是为一个已经存在的概念贴上标签,而是通过这个词,「妈妈」作为一个独立的、稳定的对象才得以从混沌的感知流中分离出来、得以「显现」。
- 名字不是外衣,而是显现的方式:名字、概念、语言不是覆盖在「真实事物」表面的一层可有可无的外衣,而是事物得以向我们「显现」的必要中介。没有「红色」这个词及其所属的色彩概念系统,我们能「看到」红色吗?我们可能感受到某种刺激,但「红色」作为一个可以被识别、记忆、交流的对象,只有在语言中才存在。
- 还原的极限:因此,所谓「悬置一切预设、回到纯粹事物本身」在海德格尔看来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幻想。当你试图剥离所有的「名字」和概念时,你得到的不是更清晰的本质,而是一片无法被把握、无法被言说、甚至无法被意识到的混沌——一个更深的「遮蔽」。
这个现象学悖论为我们理解这句歌词提供了深刻的阐释框架:
- 「名前を捨てた」可以被理解为一次激进的、类似于现象学还原的尝试:舍弃所有外在的标签、社会身份、他人的定义,试图抵达一个「纯粹的自我」。
- 「あなたのモザイクが泣いてる」则揭示了这次尝试的悲剧性结果:你没能找到一个清晰的、统一的本质,反而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更加模糊的、由无数碎片拼凑而成的「马赛克」——那个你以为隐藏在名字之下的「真我」从一开始就不存在。你只是所有名字的总和、所有关系的交点、所有他者目光的映像。舍弃了名字,你就失去了「显现」的途径,只剩下一个无法被看见、无法言说的空洞。
- 「泣いてる」成为了唯一还能证明存在的痕迹。但这哭泣声又是无声的(「音のない音」),因为没有语言、没有名字,连悲伤、痛苦都无法被准确地表达和传递。
因此,这句歌词不仅是在描述角色们舍弃了舞台名和真名,它指向的是一个更为根本的存在论困境:在一个解构了所有身份标签的世界里,主体如何显现?当所有的「名字」都被悬置,剩下的是更清晰的真实还是更彻底的遮蔽?Ave Mujica 的世界给出的答案是后者:人偶们舍弃了一切名字,却没有因此获得自由,反而陷入了更深的迷失。
而如果说现象学揭示的是「遮蔽」的维度,那么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则让我们看到「拼凑」的真相。
如果说现象学关注的是「事物如何向我们显现」,那么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关注的则是「意义如何在符号系统中生成」。这两个思潮深刻地改变了我们对语言、主体和意义本身的理解。
1. 索绪尔与结构主义语言学:能指与所指的断裂
现代语言学之父费迪南 · 德 · 索绪尔 (Ferdinand de Saussure) 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观点:语言符号 (Sign) 由两个部分构成——能指 (Signifier) 和所指 (Signified)。
- 能指:符号的物质形式,如声音、文字。例如「树」这个汉字的字形,或 /shù/ 这个发音。
- 所指:符号所指向的概念或意义。例如「树木」这个抽象概念。
索绪尔的关键洞察在于: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约定俗成的。没有什么内在的、本质的理由让「树」这个字形必须指代树木这个概念,只是我们的语言共同体达成了这样的约定。更重要的是,他指出意义不来自于符号本身,而来自于符号之间的差异关系。「树」之所以有意义,不是因为它有某个固定的本质,而是因为它不是「鼠」、不是「数」、不是「书」。意义产生于一个差异系统之中。
这个看似简单的观点却埋下了解构主义的种子:如果意义只存在于关系和差异之中,那么是否存在一个最终的、稳定的「所指」?
2. 拉康:能指的优先性与主体的碎片化
雅克 · 拉康将索绪尔的语言学洞察引入精神分析,并走得更远。他颠覆了索绪尔的公式,提出能指相对于所指具有优先性。
在拉康看来:
- 能指链 (Signifying Chain):意义不是由单个符号所承载,而是在一条由无数能指构成的链条中,通过它们之间的联系、替代、转喻和隐喻不断滑动。一个能指总是指向另一个能指,永远无法最终抵达一个确定的、在场的所指。
- 「大写的能指」(Master Signifier):在这条无限的能指链中,某些能指会被赋予一种特殊的地位,成为「缝合点」(Point de capiton),暂时固定住意义的滑动。例如「父亲」、「法律」、「国家」这些能指在特定话语中起到锚定作用。但这种锚定始终是脆弱的、暂时的。
- 主体即能指:更激进的是,拉康认为主体本身也是由能指构成的。「我」不是一个先于语言而存在的实体,而是在能指的游戏中被建构出来的一个位置、一个效应。因此,主体从根本上就是分裂的、空洞的,是一连串能指的暂时性拼凑。
这意味着,当我们说「我是谁」时,我们给出的答案——我的名字、我的职业、我的性格——都只是一个个能指。而这些能指本身又指向其他能指(名字指向家族、职业指向社会角色、性格指向过去的经历),如此往复,永无止境。那个被能指所指涉的「真实的我」永远是缺席的,我们只能在能指的镜子迷宫中追逐自己的幻影。
3. 德里达的延异:意义的永恒推迟
雅克 · 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 进一步激进化了这个思路,提出了「延异」(Différance) 这个核心概念。Différance 是一个他自己创造的词,结合了法语中「差异」(différence) 和「推迟」(différer) 两个含义。
- 空间维度的差异 (Difference):正如索绪尔所说,意义来自符号之间的差异。没有差异,就没有意义。
- 时间维度的推迟 (Deferral):但意义的生成不仅依赖于共时的差异关系,还处于一个历时的、永恒推迟的过程中。每当我们试图用一个符号来解释另一个符号时,我们只是将意义推迟到了下一个符号。就像查字典:你查「爱」,得到「深切的情感」;你再查「情感」,得到「内心的感受」;你查「感受」,又回到了「情感」…… 意义在这个循环中永远无法最终抵达。
德里达由此提出,西方哲学传统一直在追求一个「在场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Presence),即相信存在一个终极的、自明的、不依赖于任何外部中介的「在场」之物(上帝、理性、真理、本质)。而解构主义的任务就是揭示,这种「在场」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幻觉。任何看似自明的、中心的概念,其实都依赖于它所排斥、所边缘化的「他者」。
现在我们便可以更深刻地理解「あなたのモザイク」这个意象。Mosaic(镶嵌画)在艺术史上是一种用无数小块彩色石头或玻璃碎片拼凑而成的图案,这个比喻恰如其分地描绘了结构主义 / 解构主义视野下的主体:
- 「你」不是一个统一的本质,而是无数能指碎片的拼凑。你的名字、你的身份、你的角色、你的关系,这些都是一个个能指碎片,它们按照某种暂时的模式拼凑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看似完整的图像。
- 碎片之间没有本质的联系,只有约定俗成的结构。是什么让这一个个能指共同指向同一个主体?不是因为存在一个内在的本质自我作为基底,而是因为我们(以及主体自己)暂时性地将这些碎片组织在主体这个统一的框架之下。
- 一旦框架瓦解,碎片便失去了意义。「名前を捨てた」意味着那个作为「缝合点」的主能指被移除了。当名字这个锚定点消失时,那些曾经围绕着它组织起来的能指碎片就失去了连接的粘合剂,开始自由滑动、相互冲突、陷入混乱。这就是「モザイクが泣いてる」的真正含义:不是某个被遮蔽的本质在哭泣,而是那些失去了组织结构的碎片本身在哭泣,因为它们无法再形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
在解构主义的视野下,「舍弃名字」暴露的不是一个被遮蔽的真相,而是主体建构的虚构性本身。你以为「名字」只是贴在自我表面的标签,撕掉标签就能看到真实的自己。但实际上,自我本身就是由这些「标签」(能指)拼凑而成的。没有了这些能指,并不会显现出一个更真实的你,而是什么都不再剩下,或者说只剩下无法被组织、无法形成意义的碎片。
从现象学到解构主义,这两个视角共同揭示了「名前を捨てた」与「モザイクが泣いてる」之间的张力:遮蔽与碎片、隐藏与拼凑,最终都指向了同一个结论——不存在一个可以被完全揭示、可以独立于符号系统而存在的「真实自我」。
「can not, can not, not, not, not deny 紛れもなく真実」——无法否认的真相。但什么是真相?歌词中并未提及。这种含糊性本身也是 Ave Mujica 叙事的核心策略。正如制作组在访谈中提到的,「MyGO」是走「现实主义」,而「Ave Mujica」则刻意带有某种「童话气质」,让真实与虚构的边界长时间保持朦胧。于是「真相」本身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歌词只是说「无法否认」,却不告诉你否认的是什么。
「さあ 預けて 回帰するように / エネルギーはサイクル そう 今は無重力」——请你托付于我,就此归来 / 能量循环往复,此刻已然失重。「回帰するように」这个词很微妙——「回帰」意味着过去曾经有过联系,但中间断裂了,现在要重新连接。托付、回归、能量循环、失重,这一系列意象指向了某种周而复始的运动:乐队组建、解散、重组,人格分裂、融合,关系靠近、疏远、重新靠近。这里「無重力」一词很关键,失去重力意味着脱离了人们所在的世界,悬浮在某个没有稳定参照系的空间。这也正是后续剧情的一个写照:无论是 Ave Mujica 这个乐队,还是每位成员的精神状态、处境,一切都无法真正稳固下来,因为从一开始,这个世界就没有「重力」——没有稳定的秩序,没有稳定的关系,只有不断循环的创伤。
「象徴的なパレード この月夜に仰げよ仰げ / ‘completeness’ / 嗚呼 命の灯を掲げ」——象征性的游行,举目仰望月夜 / 「完好无缺」 / 高举生命之灯。这句歌词将多个意象层叠在一起,构成了一幅仪式化的图景。
先看「象徴的なパレード」(象征性的游行)。游行本是一种公共的、展示性的集体行动,通常为了庆祝胜利、宣示主权、或纪念某个重大事件。但这里强调的是「象征性」——不是实质性的胜利,不是真正的庆典,而是一场纯粹为了展示符号而进行的表演。这场游行没有起点,没有终点,并非为了到达某个目的地,而是为了在行进中展示某种形象、维持某种幻觉。这正是 Ave Mujica 舞台的本质:一场精心编排的符号游戏,一场不指向任何实质内容的演出。
「この月夜に仰げよ仰げ」(举目仰望月夜)。双重的「仰げ」(仰望)强调了这个动作的强制性和重要性——不是你是否想仰望,而是你必须仰望。仰望是一种被要求的姿态,意味着你要抬起头来、看向那个悬挂在夜空中的月亮。前面已经提到,月光让人偶获得了意识,但也让她们看清了自己的处境。而这里「仰望月夜」则是要求游行的参与者(无论是舞台上的人偶还是台下的观众)共同见证这个幻觉的生成——在月光的照耀下,承认这场游行的「象征性」,承认即将展示的「完整性」。
随后便是那个突兀的英文词汇:‘completeness’。它孤零零地插入在日语歌词之中,仿佛一块异质的碎片,仿佛一个从别处嫁接过来的概念。这种语言的断裂本身就在提醒我们:「完整性」不属于这里,而是一个外来的、强加的、无法被母语承载的幻想。什么是完整?在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主体从一开始就是分裂的、残缺的。婴儿在「镜像阶段」中第一次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完整形象,产生了「我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的自我」的幻觉——但这只是想象界的产物。实际上,主体永远无法摆脱内在的分裂:意识与无意识的分裂、能指与所指的分裂、自我与他者的分裂。「完整性」只能在想象中存在,只能在镜子的反射、他人的目光、符号的游戏中暂时显现,却从未真正到来过。然而这首歌却要求你举起「完整」的旗帜,在月夜下进行一场象征性的游行。Ave Mujica 的舞台正是这样一面镜子:她们穿着华丽的服装、戴着精致的面具、组成一个「完整的乐队」,在灯光与音乐的包裹下展演一个关于「完美的整体」的童话。但台下的观众都心知肚明:这个「完整」随时都可能崩塌。这场游行展示的不是完整,只是一种对完整的渴望,以及对这种渴望永远无法实现的清醒认知。
最后是「嗚呼 命の灯を掲げ」(啊,高举生命之灯)。「掲げる」这个动词通常用于举旗帜、标语、火炬——一个公开的、展示性的动作。生命之灯不是为了照亮自己的路,而是为了被他人看见,为了在这场象征性的游行中成为一个可见的符号。火焰 / 灯火在文学传统中常常象征着生命力、激情、希望,但这里的「命の灯」更像是一个被要求展示的道具:你要高举它,让它成为这场游行的一部分,让它证明你还「活着」,即使「活着」本身也只是一场表演。而「嗚呼」这个感叹词更透露出一种复杂的情绪:是悲叹?惊叹?认命?抑或是讽刺?它就像是在说:看哪,我们正高举着生命之灯,我们正展示着完整性,我们正在月夜下游行——但这一切都不过是一种象征、一个符号,是一场明知会破灭却还要演下去的幻觉。
接下来是副歌:「KiLLKiSS judy.., KiLLKiSS jude.., KiLLKiSS juda.. / 欺いて / 抱きしめて」。「KiLLKiSS」显然指向犹大之吻——以亲吻来背叛、以拥抱来谋杀。三个名字的变体:judy / jude / juda,暗指同一个人拥有三副面孔。欺骗(欺いて)与拥抱(抱きしめて)在同一个动作中完成,预示了作品中人物关系的复杂底色:爱可能同时也伴随着谎言与伤害。
「ねぇ 無防備だね 美しい戯れに 人は壊れてゆく / 可笑しいわね」——真是毫无防备啊,甜美嬉戏令人毁于一旦,多么可笑。这里的「戯れ」(嬉戏 / 玩耍)把毁灭过程轻描淡写地描述成一场游戏,但「人は壊れてゆく」(人毁灭下去)却是确凿的事实。「可笑しい」,可笑又荒诞——在美丽的表象下,毁灭正在发生,而这一切竟被当作某种奇异的美学来展示,这也正是 Ave Mujica 舞台的写照。
「‘cuz we’re all alone」——因为我们都是孤独的。在前面分析「马赛克」意象时我们已经看到,当主体舍弃了所有名字、所有能指,剩下的并非某个纯粹的本质,而是更彻底的遮蔽与碎片化。现在歌词直接揭示了这种状态的情感内核:孤独。这不是某种可以通过陪伴或理解来消解的、浅层的孤独感,而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结构性的孤独——拉康所说的主体与「大他者」之间永恒的断裂。我们每个人都被困在各自的「私の世界」中,即使站在同一个舞台上、唱着同一首歌,每个人偶仍然是孤立的、无法真正抵达彼此。但这种孤独不是一个需要被克服的问题,而是 Ave Mujica 世界的前提条件。
「噛み締めても まだ痛むなら / 手を挙げ 希え」——倘若细品仍旧疼痛,高举双手、虔诚祈愿。「噛み締める」这个动词原意是咀嚼、仔细品味,这里用来描述对痛苦的反复咀嚼。你已经试图内化这个痛苦、消化这个创伤,但它依然疼痛,那么你唯一的选择就是「手を挙げ」、「希え」,举起手来、祈求救赎。但向谁祈求?在一个「大他者」缺席的世界里,这种祈求注定是虚空的。Ave Mujica 的舞台正建立在这种虚空的祈求之上:没有神灵会回应,没有救赎会降临,但人偶们还是要举起手来,因为这种「举手」的姿态本身就是演出的一部分,是将内在的痛苦外化为可见符号的必要动作。
「oh, when you bleed, 惑星に そう その影を伸ばせ / ねぇ 私の世界(ほし)が知りたがっているわ さあ」——当你流血时,在行星上投下阴影,我的世界正渴望知晓。这里「世界」与「星(ほし)」是一处双关,而「私の世界」强调的是一个完全自我中心的、封闭的空间。痛苦在这里被彻底景观化了,正如鲍德里亚在分析当代社会时就曾指出的,一切都在被转化为景观、转化为可供展示和消费的符号。而 Ave Mujica 的舞台正是这样的逻辑:既然痛苦无法被消化,那就把它展示出来;既然伤口无法愈合,那就用它来书写。「when you bleed」(当你流血时),流血不是需要包扎,而是一次展演的开始。你的血液要「在行星上投下阴影」,成为天空中可见的图案,要成为「我的世界」渴望观看的奇观。谁的世界?不仅是角色们的世界,更是每位台下观众的世界。
「you bleed, yes, bleed その血で 天(そら)の五線譜を書き換えれば」——你的血液,若能改画为天空的五线谱。血液书写音乐,这个意象将创作的过程残酷化了。音乐不再是灵感的产物、情感的自然流露,而是用生命本身、用身体的损耗「改写」出来的。「天の五線譜」暗示了某种预先存在的秩序、某种既定的模板,而你要做的是用自己的血液去「书き換える」(改写 / 重写)它。这呼应了前面「回帰」的意象——不是创造新的东西,而是对已经存在的模式进行又一次的重写。每一次的「改写」都需要付出血的代价,但结果仍然是写在同一张五线谱上,无法逃出既定的框架。
「code ‘KiLLKiSS’」的表述尤其值得注意。「code」(代号 / 代码)一词的出现将整个过程祛魅了——所有这一切并不是一场自发的、浪漫的艺术创作,而是一个被编码的、预先设定的程序 / 计划。「KiLLKiSS」只是一个「代号」,是一个在剧本中早已写好的事件。「代号」暗示了一种宿命论,暗示所有这些看似偶然的崩溃其实都是必然的、被某种更深层的结构所决定的。这实际上也是与开头「弄られて垂れ流す」的呼应,同时暗合「颂乐人偶」的隐喻。
最后是「ねぇ あからさまね 醜い終局に すべてが変わってゆく / 儚いのね / そう このまま 壊れて」。
「あからさま」意为露骨、明目张胆,这个词的出现标志着从隐蔽到暴露的临界点。前面的歌词一直在用隐喻、符号、美丽的包装来言说痛苦,到最后连这层包装都要被撕开了。所有被「名字」遮蔽的东西、在「马赛克」背后哭泣的碎片、用华丽舞台效果掩盖的创伤,最终都会「明目张胆」地暴露出来。这种暴露是 Ave Mujica 的结构内在的必然走向——建立在谎言与遮蔽之上的梦境不可能永远持续,「code ‘KiLLKiSS’」早已编入了这个暴露的时刻。面具终会被摘下、身份终会被揭穿、真相终会浮出水面。在故事的终局,一切精心维护的幻象都将瓦解。
从「美しい戯れ」(美丽的嬉戏)到「醜い終局」(丑陋的终局),歌词完成了一次翻转。美丽从一开始就只是表象,精心布置的符号底下承载的终究还是那些无法愈合的创伤、无法消化的痛苦。当这些被掩盖的「丑陋」最终暴露,「终局」也就到来了。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歌词预言的不是某种「拨云见日」式的真相大白,而是一种虚无——无论掩盖还是揭露,无论美丽还是丑陋,崩溃、毁坏都是唯一的结局。
「儚いのね」(多么缥缈)。这个词呼应了前面的「無防備」(无防备)与「可笑しい」(可笑),形成了一组情绪上的递进:无防备的脆弱(人偶们毫无防备地被命运所玩弄)、可笑的荒诞(毁灭竟被当作美学奇观来展示)、缥缈的幻灭(一切本就是空中楼阁、镜花水月)。「儚い」这个词在日语中承载着强烈的文化意涵,它常用来形容樱花的短暂、人生的无常,带有一种物哀美学的色彩。但这里的「儚い」已经脱离了那种温柔感伤的抒情传统,转而成为一种冷酷清醒的自我认知——正因为知道一切都是虚幻的,所以更加清醒地意识到这种虚幻本身的荒诞性。这种虚幻不再需要被赋予某种物哀式的诗意。
「そう このまま 壊れて」(就这样毁坏吧),可以说是整首歌最后决定性的宣言。「そう このまま」(就这样)——不加修饰、没有转折,只是平静地接受。「壊れて」是祈使语气,但同时又像是一种邀请、一种接纳——让我们就这样毁坏下去吧。这种「毁坏」不是某个具体事件的终结,而是一种持续的、反复的、永无止境的循环状态,是一种存在方式——「Fluctuat nec mergitur」(风吹浪打,亦不沉没)。不沉没并不是因为船只本身足够坚固,而是因为已经放弃了抵抗,选择与毁灭共存。
从第一句开始,整首歌就已宣告了它的立场:「Ave Mujica」不会是某种成长叙事或救赎童话,而是一场清醒的、审美化的、命中注定的自我毁灭。Ave Mujica 这个舞台存在的理由就是为那些无处安放的创伤、无法被主流叙事接纳的痛苦提供一个暂时的收容所——即使这个收容所毁灭的结局早已注定。
05:01

在日本音乐文化的符号体系中,武道馆大概是最具标志性的圣地之一,无数传奇乐队都曾将「站上武道馆的舞台」作为职业生涯的里程碑。在少女乐队题材的叙事传统中,武道馆更是那个遥不可及的终极目标、梦想中的舞台。无论在虚拟作品还是现实世界中,武道馆无疑都是需要乐队成员们经历无数挫折、齐心协力通过种种考验才终于抵达的彼岸,是宏大叙事里经典的终点站。
然而 Ave Mujica 却把武道馆作为开局,此时第 1 集才刚过去 5 分钟。
剥夺「成为」的可能性
传统少女乐队叙事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可以说是「成为」。角色们从无到有、从默默无闻到万众瞩目,整个叙事就是一部关于「如何成为」的编年史。观众跟随角色一同经历每一次小小的胜利、每一个阶段性的进步,最终达到故事的高潮——登上武道馆、站在聚光灯下,至此完成了一次情感的集体宣泄,台上的角色和台下的观众都无比感动。这种叙事预设了一个线性的时间观:过去不完美、未来可期待,我们立足的现在是通往未来的阶梯。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进步主义的世界观。
但「Mujica」从一开始就拒绝了这个游戏。武道馆出现在了开头,「成为」的过程被完全省略。没有成长曲线,没有从校园舞台一步步向更高处攀登的励志叙事,Ave Mujica 第一次进入观众视野时就已经站在了传统意义上的顶点。既然终点在开头就已抵达,那接下来还能去哪里?
答案很明显,这个故事要展示的是「如何坠落」。很多观众喜欢自作主张地预设一个成长叙事,然后因为作品没能满足自己的心理预期、没按自己设想的轨迹走就直呼「人物塑造烂完了」、「你的角色弧光在哪里?」但实际上作品从一开始就已经摆明了,这就不是一个成长叙事的模板。大体上,我们可以认为「Mujica」是前作「MyGO」的镜面翻转:如果说「MyGO」是迷途之子跌跌撞撞向上攀爬,那么「Mujica」则是人偶们一步步向下坠落。一般少女乐队观众在偏好上自然会更倾向于前者,这是他们熟悉的舒适区。而如今我们可以意识到,整部「MyGO」其实是为了「Mujica」这碟醋包的饺子,是一个结构上的铺垫。
不存在可以成长的「人」
从更深的理论层面来看,这个开局还标志着一种对人文主义主体的拒绝。
传统成长叙事的哲学前提是什么?是源于启蒙主义的理性主体观,即相信「人」作为历史的主体、作为自身命运的主宰,可以通过自我完善不断进步。但正如前言中论述的,「Mujica」呈现的是福柯意义上「人已死」的世界。这里不存在可以自主成长的理性主体,只有被结构、话语、创伤所操控的「人偶」。在这样的世界里,武道馆不可能是「成长」的终点,因为「成长」这个概念本身就已失效。
为什么说「成长」失效了?因为这个概念高度依赖一个形而上学的预设:存在一个连续的、统一的、拥有自由意志的「主体」。我们天真地以为有一个不变的内核叫作「自我」,它像容器一样承载经验、积累知识,沿着时间的线性轨道不断向前,最终抵达某个「更好」或「更完整」的状态。
但这只是启蒙理性编织的美梦。
在继续论述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引入一个关键的批判视角:齐泽克对成长叙事作为意识形态装置的分析。
斯拉沃热 · 齐泽克 (Slavoj Žižek) 继承拉康和马克思的双重传统,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我们所相信的「成长」,从根本上就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装置之一。
齐泽克指出,意识形态的功能不是让我们「相信」某种虚假意识——现代人早已不再天真。意识形态真正的力量在于让我们「明知如此,却仍照旧为之」。他有句名言:「他们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但他们仍然这样做。」(They know very well what they are doing, but still, they are doing it.)
成长叙事正是这样的幻象结构。它向我们承诺一个简单的线性逻辑:努力 → 进步 → 成功 → 完整的自我。只要你不断提升自己、积累经验、克服困难,你就能成为「更好的人」,就能抵达那个圆满的终点。
但这个承诺掩盖了什么?
首先,它掩盖了拉康意义上的根本「匮乏」。在拉康的理论中,主体的匮乏是结构性的、无法被填补的——我们永远无法成为完整的存在,因为主体本身就建立在一个根本的缺失之上。但成长叙事告诉我们:匮乏是可以被克服的,只要你足够努力。
这个谎言有什么功能?它让我们不断追逐那个永远无法抵达的「完整自我」。今天你获得了学位,明天你要升职,升职了还要买房,买房了还要实现财务自由…… 每一个「成就」都只是暂时填补了匮乏,随即又产生新的匮乏。你永远在路上,永远在「成长」,永远不满足。
齐泽克称这种机制为「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那个「完整的自我」、「理想的人生」就是这样的崇高客体——它必须永远保持在地平线上,既激发欲望又永远无法获得。一旦你真的抵达了,幻象就会破灭,于是系统会立刻为你设置新的目标。
更重要的是,成长叙事将所有的失败都归咎于「个人不够努力」。你没有成功?那是因为你还没成长到位。你感到空虚?那是因为你还需要继续提升自己。这种逻辑完美地掩盖了结构性的问题——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有问题,是你还不够好。
于是成长叙事就成为了最完美的意识形态装置:它让主体自愿地、积极地参与到自我剥削中。你不需要外部的强制,你就会主动地「投资自己」、「优化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而这一切都在为资本的增殖服务。你的「成长」就是你的「增值」,就是你在人力资本市场上的竞争力提升。
齐泽克犀利地指出:当代资本主义最大的成就,就是让剥削看起来像是自我实现。
「Mujica」的社会批判目的在此已初见端倪。为什么要拒绝成长叙事?因为一旦接受了成长叙事的框架,就意味着接受了这个意识形态的幻象结构——相信存在一个可以通过努力抵达的「更好的自己」,相信匮乏是可以被填补的,相信「成为」是可能的。
武道馆的开局其实就是直接快进到结果,将传统作品中作为结局的部分放到一开始,继续讲之后的故事。然后你会「惊奇」地发现,即使已经站在武道馆、实现了你的梦想 / 人生目标,匮乏依然存在。这就像是一些传统 Galgame 将结婚作为故事的终点,然而真正的故事并不会在此结束——然后呢?
所谓的「终点」其实什么都不会解决。即使你抵达了那个被承诺的终点,你依然是破碎的、匮乏的、不完整的,因为匮乏从来不是通过「成长」就能填补的——它是主体存在的根本条件。更进一步地说,所谓的「成长」本身就是一场表演,一个为了维持某种幻象而必须不断重复的仪式。站上更大的舞台并不意味着成长为更好的人,很多时候只是更彻底地内化了意识形态的规训。
所以我们现在就能理解为什么「Mujica」要以武道馆作为开局——不仅是剥夺「成为」的叙事,更是宣告「成为」本身的不可能,因为本就不存在可以成长的「人」。
05:11

当被采访者提问对即将登上武道馆有什么感想时?睦沉默了。为什么睦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在正常的成长叙事剧本中,这个问题有一套现成的回答模板:「非常激动」「感谢大家的支持」「会继续努力」…… 这些话构成了娱乐工业、偶像文化、励志叙事共同编织的话语体系——一套关于「努力 → 成功 → 幸福」的意识形态修辞。
但睦说不出来。
不是她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恰恰相反,作为知名演员的女儿、从小生活在聚光灯下的她太清楚在这种场合应该说什么样的话了。她继承了母亲的演技天赋,能够无缝切换不同角色,按理说这样的「标准答案」对她来说应该是信手拈来。
但她就是说不出来。
这里发生的不是「不会演戏」,而是一种更深层的失败:意识形态的话语机制在睦这里失灵了。齐泽克指出,意识形态的运作依赖一个关键机制:让主体「明知如此,却仍照旧为之」。你心里清楚那些话语是空洞的,但你仍然可以说出来、表演出来、让自己相信「说出来就够了」。这种犬儒式的参与正是晚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特征。
但睦连这种犬儒式的参与都做不到了。
在拉康的理论中,「症候」是真实界冲破符号界秩序时留下的裂痕,是无意识欲望的痕迹、语言的漏洞。这里睦的沉默正是这样的症候,当意识形态话语在她的喉咙里卡住、无法顺畅说出时,这个裂缝就暴露了。她无法说出那些「标准答案」,因为她已经隐约感知到:登上武道馆不会带来任何真正的改变。像是若麦引以为傲的「最速登上武道馆」之类的成就只是一个幻象,是意识形态为了维持运转而设置的「崇高客体」,一旦真正抵达就会幻灭。睦不知道如何用语言表达这个真相,她没有理论工具、没有批判意识,只有一种模糊的、难以言说的不安感,但这种不安感已经足以让她无法流畅地说出那些虚假的话了。
从另一个角度,睦的沉默不仅关于未来,也关于过去。在 CRYCHIC 解散时,睦说了一句话:「我从没觉得玩乐队开心过……」这句话成为压垮 CRYCHIC 的最后一根稻草,也成为睦永远无法原谅自己的创伤记忆。她将乐队的毁灭归咎于自己说错了话,从此对语言本身产生了深深的恐惧,害怕自己的话又会再次毁掉什么。所以当采访者问她有什么感想时,睦面对的不仅是「应该说什么」的问题,更是「说了会怎样」的恐惧。如果她不慎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感受:「我从没觉得登上武道馆有什么意义……」「不会长久……」恐怕又会重蹈覆辙。于是她选择了最安全的选项:什么都不说。沉默至少不会主动伤害任何人,不会成为新的导火索。但这种自我审查式的沉默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对自己的暴力,这种压抑也为后来睦精神状态的恶化埋下伏笔。
讽刺的是,睦的直觉是对的。武道馆根本不是梦想的终点,而是噩梦的开始。
06:05

作为追求爆点的自媒体博主,若麦对面具的不满几乎可以说是一种本能反应。不过这种「本能」是从何而来?若麦并非天生就对爆点如此敏感,这种本能实际上是她长期浸淫于当代媒介生态的产物。要理解若麦的行为逻辑,就得先理解她所处的这个系统如何运作,以及这个系统是如何塑造了像她这样的内容生产者的思维方式。
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
居伊 · 德波 (Guy Debord) 是法国激进思想家、情境主义国际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 的核心人物。他在 1967 年出版的《景观社会》(La Société du Spectacle) 中提出了一个极具预见性的论断:「在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的庞大堆聚。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转化为一个表象。」
德波所说的「景观」(Spectacle) 并非简单指代影像或演出,而是指一种社会关系的总体性异化状态。在景观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直接关系被影像所中介,真实的生活体验被表象所取代。景观不是影像的集合,而是「以影像为中介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
这个理论的核心洞察在于: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生产的目的不再是满足人的需求,而是生产出更多可供观看、可供消费的景观。人们不再直接生活,而是观看生活的表象;不再拥有真实的经验,而是消费关于经验的影像。
鲍德里亚的拟像理论
让 · 鲍德里亚 (Jean Baudrillard) 继承并激进化了德波的理论。在《消费社会》(La Société de consommation) 中,他指出当代社会已经从生产物品的时代进入了生产符号的时代。我们消费的不再是物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它们所承载的符号意义、它们在符号体系中的位置。
更进一步,鲍德里亚在《拟像与仿真》(Simulacres et Simulation) 中提出了「拟像」(Simulacra) 理论。他将符号与现实的关系分为四个阶段:
- 反映基本现实:符号是对现实的忠实再现(例如文艺复兴时期的写实绘画)
- 掩盖和歪曲现实:符号开始歪曲现实(例如意识形态宣传)
- 掩盖现实的缺席:符号假装指向一个并不存在的现实(例如迪士尼乐园)
- 与现实无关:符号成为纯粹的拟像,它不再指向任何现实,而是自我指涉(例如当代的超真实)
在第四阶段——我们所处的当代社会——拟像不仅取代了现实,甚至比现实更加「真实」。这就是「超真实」(Hyperreality) 的状态:模拟先于被模拟之物而存在,影像比实物更具说服力,表象比真相更能打动人心。真实性本身已经失去价值,只有被转化为景观、被展示、被观看的东西才具有价值。你的痛苦如果没有被拍成视频、没有获得点击量就不存在,你的成就如果没有被晒在社交媒体上、没有收获点赞就没有意义。生活的意义不在于你真实地体验了什么,而在于你展示了什么、别人看到了什么。
注意力经济的运作逻辑
注意力经济 (Attention Economy) 这个概念最早由心理学家赫伯特 · 西蒙 (Herbert A. Simon) 在 1971 年提出。他敏锐地观察到:「在信息丰富的世界里,信息的丰富意味着其他东西的稀缺——这个其他东西就是信息所消耗的东西。信息消耗的是接收者的注意力。」
在互联网时代,这个洞察变得更加尖锐。信息过载导致注意力成为最稀缺的资源,内容生产者之间的竞争本质上就是对用户注意力的争夺。注意力经济催生了一套独特的「爆点逻辑」:
- 反转叙事永远比平铺直叙更有传播力(你以为是 A,其实是 B)
- 身份落差总能引发围观(知名人士的隐藏身份、光鲜背后的真实面目)
- 冲突比和谐更容易被转发(和谐不产生流量,矛盾才会被分享)
- 即时性决定价值(第一个爆料的人获得最大收益,过时的信息无人问津)
在这套逻辑下,内容的真实性、深度、价值都让位于它的传播性。重要的不是你说了什么,而是有多少人看到了你说的;不是内容本身的质量,而是它能否在信息洪流中脱颖而出、抓住那转瞬即逝的注意力。更重要的是,注意力经济塑造了一种新的主体性。在景观社会中,「被看见」成为存在的前提条件。人们不是为了生活而展示,而是为了展示而生活;不是先有了体验再分享,而是为了分享而去获取可供分享的素材。自我认同不再来自内在的反思,而来自外部的点赞数、转发量、评论区的反馈。主体成为一个永远需要被他者目光确认的空洞能指。
Ave Mujica 的设定本身就已经制造了一个悬念结构:戴着华丽面具的神秘乐队、成员身份不明。而若麦清楚地知道这些成员并非无名之辈,像祥子、初华的身份天然就自带话题性和流量。只要揭示面具之下的真实身份,点击量、转发量、讨论热度都可以预见。然而面具的存在却让 Ave Mujica 保持在一个封闭的符号系统内部,无法完全纳入景观社会的消费逻辑。在若麦看来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在她的价值观里,所谓艺术性、神秘感都远不如流量、热度来得实在,或者说今天营造的艺术性、神秘感最终也是要为流量、热度服务的,面具的存在就是为了揭下的那一刻。毕竟在注意力经济的游戏规则下,不被看见就等于不存在。
但如今我们已经知道,拉康意义上的主体匮乏是结构性的、无法被填补的。若麦这种将自我认同完全托付给外界反馈的主体,本质上就是注意力经济塑造出的空洞能指。流量、热度不仅无法填补匮乏,反而会让主体陷入无止境的追逐:今天达到了十万播放量,明天就需要百万;百万达成了,又要追求千万。若麦越是依赖外部的认可,就越是无法建立起内在的、稳定的自我价值感。她会需要不断制造新的爆点、不断维持热度,否则一旦哪天热度消退,她就会陷入存在性的焦虑——「我还剩下什么?」
06:12 - 06:14


喵姆老师极具冲击性的洞察,已收录进「Mujica」名人名言。
「就算昨天喜欢,今天也厌倦了。」若麦的这句话切中了当代媒介消费的要害。昔日还在疯狂追捧的偶像,今天就已过气、被人遗忘;上个月还在刷屏的热点,今天早已无人问津。观众的喜新厌旧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内容创作者必须不断制造新鲜感才能维持热度。从这个角度看,若麦执着于揭开面具、制造爆点的焦虑也就不难理解了——她深知自己服务的这个市场有多么善变。
初看之下,这似乎完全是观众的问题:贪得无厌、喜新厌旧,今天能把你捧上天、明天就把你踩在脚下。许多创作者都会陷入一种道德化的指责:观众太肤浅了、太浮躁了、太没品位了,然而真相远比这复杂。观众的善变并非源于道德缺陷或品味低下,而是和上一节讨论的创作者的思维模式一样,本身也是被当代媒介生态所塑造的产物。创作者和观众实际上被困在同一个陷阱里,双方都是受害者。
从固态到液态:现代性的转变
齐格蒙特 · 鲍曼 (Zygmunt Bauman) 是 20 世纪末至 21 世纪初最重要的社会学家之一。他在晚年的一系列著作中提出了「液态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 这个核心概念,用以描述当代社会的根本转型。
在鲍曼看来,古典现代性是「固态」的——它建立在稳定的制度、长期的规划、持久的关系之上。工厂制度、终身雇佣、婚姻承诺、民族国家,这些都是固态现代性的典型产物。人们可以做出长期承诺,因为世界相对稳定可预测。
但当代社会已经进入「液态现代性」阶段。液体的特性是什么?流动、易变、不固定。液体无法保持形状,只能暂时适应容器;一旦容器改变,液体就立刻改变形态。鲍曼认为,当代社会的一切——工作、关系、身份、价值观——都呈现出这种液态特征。
液态现代性的核心机制:消费主义
鲍曼指出,液态现代性的核心驱动力是消费主义逻辑的全面胜利。在生产主义时代,资本主义需要的是服从纪律、延迟满足、长期规划的工人;但在消费主义时代,资本主义需要的是不断追求新鲜刺激、拒绝延迟满足、永不满足的消费者。
消费主义的关键在于,它必须不断制造「不满足」。如果消费者满足了,消费就会停滞,资本增殖就会停滞。因此消费主义的核心任务就是确保没有任何欲望能够被真正满足,确保每一次消费都只是暂时缓解焦虑,随即产生新的欲望。
鲍曼提出了一个关键概念:「消费者社会」(Consumer Society)。在这个社会中,人不再仅仅是偶尔消费的生产者,而是首先被定义为消费者。更重要的是,人们不仅消费商品,也消费关系、消费体验、消费身份。一切都可以被消费,一切消费都是短暂的。
短暂性作为结构原则
在液态现代性中,短暂性 (Transience) 不再是偶然的副作用,而是系统的结构原则。商品被设计成易损耗的,因为耐用品会威胁持续消费;关系被设计成随时可替换的,因为长期承诺会妨碍灵活性;身份被设计成不断重塑的,因为稳定的自我不需要购买新的符号来表达。
鲍曼指出,当代文化产业最擅长的就是制造「瞬时性事件」。每一个热点、每一次刷屏、每一个爆款,都被精心设计成只能维持极短时间的高峰,随即迅速衰退,为下一个热点让路。这样的节奏确保观众永远处于追逐的状态,永远来不及深入思考,永远需要新的刺激。
人际关系的液态化
鲍曼在《液态之爱》(Liquid Love) 中分析了亲密关系在液态现代性中的命运。他指出,当代人际关系越来越呈现出「连接」(connection) 而非「关系」(relationship) 的特征。
连接的特点是:随时可以建立,随时可以断开;不需要深度投入,不需要长期承诺;就像社交媒体上的关注和取关,轻点鼠标就能完成。这种连接模式虽然灵活便捷,却无法提供真正的情感支撑和归属感。
鲍曼犀利地指出:「在液态现代性中,最大的恐惧是被抛弃,但同时最大的诱惑也是保留抛弃他人的自由。」人们既害怕孤独,又害怕承诺;既渴望稳定的关系,又渴望随时更换的自由。这种矛盾心态使得一切关系都变得脆弱而短暂。
液态自我与身份焦虑
在液态现代性中,自我身份也失去了稳定性。你今天是这样的人,明天可能就要重新定义自己。职业不再是终身的,技能很快会过时,今天的专家明天可能就要重新学习。
这种不稳定性制造了深刻的焦虑。你永远无法确定自己是否足够好,因为「足够好」的标准本身也在不断变化。你必须不断学习、不断适应、不断重塑自己,才能避免被时代抛弃。
鲍曼指出,消费文化为这种焦虑提供了虚假的解决方案:购买新的商品、更新形象、追逐潮流。但这些解决方案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它们不断强化「你现在还不够好」的信息,从而制造更多的焦虑和更多的消费欲望。
现在我们可以理解,「就算昨天喜欢,今天也厌倦了」的心态本质是液态现代性的必然产物。观众被训练成永不满足的消费者,他们的注意力、情感都成了液态的、流动的、随时可替换的,这种训练来自整个消费主义文化的日常浸润。电子产品要经常换新,衣服要紧跟最新的潮流,观众对偶像、对内容的喜新厌旧,也只是他们在消费主义文化中习得的行为模式在文娱领域的再现。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液态现代性剥夺了深度投入的可能性。当一切都是短暂的、随时可替换的,人们也就失去了建立长期承诺的能力。每个人都学会了保持距离、保持冷漠、不轻易投入自己的感情,时刻保持一种玩世不恭的「乐子人」心态。这种心态看似是自我保护,实际却让自己陷入了更深的孤独。
鲍曼的液态现代性理论揭示了宏观的社会结构转型,但观众的喜新厌旧还有更具体的技术性成因。在微观层面,当代媒介技术是如何一步步将人类的注意力碎片化、将深度阅读能力消解的?这就需要我们引入认知科学和媒介技术的视角。
信息过载的认知后果
心理学家和认知科学家早已发现,人类的注意力容量是有限的。米哈里 · 契克森米哈 (Mihaly Csikszentmihalyi) 在研究心流理论时指出,人类意识每秒钟只能处理约 126 比特的信息,这个容量在数千年来基本没有变化。
然而信息环境却发生了爆炸性的变化。社交媒体、新闻推送、视频平台、即时通讯工具不断向我们投喂信息,远远超出了大脑的处理能力。这种信息过载带来的第一个后果就是注意力的碎片化。当信息量远超处理能力时,大脑会采取「浅层扫描」模式:快速浏览、提取关键词、立即判断是否值得继续投入注意力。这种模式在进化上是有意义的,它帮助我们在危险的环境中快速识别威胁。但在当代信息环境中,这种模式意味着我们失去了深度阅读、深度思考的能力。
注意力经济与设计成瘾
科技公司深知注意力是稀缺资源,于是将整个商业模式建立在对注意力的争夺上。算法被设计成最大化「用户参与度」,即让用户尽可能长时间地停留在平台上。
前 Google 设计伦理学家特里斯坦 · 哈里斯 (Tristan Harris) 揭露了这个行业的核心策略:利用人类心理弱点设计成瘾机制。无限下拉刷新、推送通知、点赞数字,这些设计都在利用人类大脑的奖励回路,制造「间歇性强化」效应,让用户形成强迫性使用习惯。更关键的是,算法会不断测试什么样的内容最能抓住你的注意力,然后向你推送更多类似内容。这个过程中,算法学会了绕过你的理性思考,直接刺激情绪反应——愤怒、震惊、恐惧、好奇,这些原始情绪最容易引发点击和分享。
推荐算法的同质化陷阱
推荐算法的另一个后果是内容的同质化。算法根据点击率、完播率、转发量来判断内容的价值,这导致了一个恶性循环:创作者为了迎合算法而生产相似的内容,算法又根据这些数据向用户推荐更多相似内容,用户的品味被算法塑造得越来越窄。
这种机制下,任何需要深度投入、需要背景知识、需要耐心思考的内容都处于劣势。相反,那些能在三秒内抓住注意力、不需要任何背景知识、立即给出情绪刺激的内容会被优先推荐。长此以往,整个内容生态就会向最浅层次、最简单粗暴的方向退化。
永恒的现在时
媒体理论家道格拉斯 · 拉什科夫 (Douglas Rushkoff) 提出了「永恒的现在时」(Present Shock) 的概念。在信息洪流中,过去和未来都失去了意义,只有「此刻」存在。上一秒的新闻已经是「旧闻」,下一秒的热点还未到来,人们的意识被永久固定在一个没有纵深的瞬间。
这种时间感的崩塌使得任何长期规划、任何需要耐心培养的东西都变得困难。观众无法对一个艺人保持长期关注,因为「长期」这个概念本身已经瓦解了。今天喜欢、明天厌倦,因为「今天」和「明天」之间已经隔着无数个信息洪流冲刷出的断层。
值得一提的是,这篇文章的形式本身就是对注意力经济的反叛。毫无吸引力的封面和标题、动辄数万字的篇幅、密集的理论铺陈,这些都是刻意为之的「反注意力」设计。我拒绝迎合碎片化阅读的习惯,也拒绝那些已经丧失深度阅读和深度思考能力的读者——即使理解了背后的系统性机制,我也不同情那些无法看穿陷阱、或者「明知如此,却仍照旧为之」的人。这种形式是一道天然的门槛,会自动劝退那些我不想见到的读者。反正我也不需要做什么爆款,真要成了「出圈爆款」反倒是件恐怖的事,评论区将是怎样一片群魔乱舞不难想象。
但另一方面,对于有意愿阅读的人,这种尽可能详尽阐述、补足所有必要理论基础的形式也不存在故弄玄虚、建立文化壁垒的倾向——我并不筛选知识储备,这些都是可以后天习得的,只要还有这个意愿。
若麦深知这一切。作为自媒体博主,她知道观众的注意力早已碎片化、被驯化成只能维持极短时间的兴奋。她知道自己必须不断制造新的爆点,因为一旦停下来,算法就会把观众推送给下一个更新鲜的目标。她其实也知道即使揭开面具能带来一时的流量,这个热度也维持不了太久,很快就会被下一个爆点取代。这也是为什么若麦会如此焦虑,因为她明白自己是在和整个系统的短暂性赛跑,而这是一场注定会输的比赛。
至此,创作者和观众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一种共谋。创作者迎合算法、追逐爆点,生产出更多短平快的刺激性内容;观众的注意力在这种训练下变得更加碎片化、更加善变;算法根据这些数据进一步优化推荐机制,向创作者传递「这就是观众想要的」的信号。于是整个系统螺旋式下沉,所有人都被困在一个没人想要、却没人能逃离的陷阱之中。
若麦对面具的不满,观众的喜新厌旧,本质都只是这个系统运作的表征。真正的问题不在个人,而在于液态现代性和注意力经济共同构建的这个结构性陷阱。在这个陷阱中,无论是创作者还是观众都失去了建立深度关系、进行深度投入的能力。大家都在追逐转瞬即逝的刺激,都在用短暂的兴奋掩盖深层的空虚,都在假装自己还拥有选择的自由——但实际上,每个人都只是这台巨大机器上的零件,按着预设的程序在运转。
若麦固然是被注意力经济所操纵的人偶,身处这个时代的观众亦如是。
06:41 - 07:54

不是「我想和你一起实现某个梦想」,而是「和你一直在一起」就是梦想本身。初华(初音)深情的告白本就令人动容,细想她话语背后的心境则更是觉得沉重。
一切都要从初音的处境讲起:她是丰川家的私生女。这个身份意味着她从一开始就被剥夺了「成为自己」的资格。没有合法的名字,没有被承认的身份,她必须顶替妹妹的名字才能在这个世界有自己的容身之处,必须假装成另一个人才能被看见。在这种处境下,初音面对的可以说是存在本身的匮乏。她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甚至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资格去「想要什么」。当一个人连自我都是借来的、伪装的,又如何能有真正意义上「自己的梦想」?所谓「成为偶像」之类的目标,都是妹妹初华的,而不是她自己的。她从一开始就活在他人的影子里,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被掩盖的秘密。
而那个夏夜改变了这一切。当初音假扮妹妹陪祥子观星时,祥子说她「如月亮一般柔和」。这句话对其他人来说或许只是随口一言,但对初音来说却是第一次——这是第一次有人看着她、对她说出「你是什么样的人」的评价。不是「你应该成为什么样」,而是「你就是这样」。祥子的这句话给了初音一个关于自己的形象,一个完整的、美好的、属于她自己的形象。正是在这个瞬间,初音第一次感受到了自己真实的存在。不再是另一个人的替身,不必是需要被隐藏的污点,而是一个能被看见的、真实的「人」。祥子的目光就是拉康的那面镜子,让初音第一次看到了一个「完整的我」。
从此,我因你的目光而存在,因你的话语而获得了形状。
所以当初音说「我的梦想就是和你一直在一起」时,背后还有一个更悲伤的原因:因为只有在祥子身边,她才能确认自己的存在,「和祥子在一起」就是她存在的全部意义。一旦失去祥子,她就会重新回到那个没有名字、没有形状、无法辨识自己是谁的虚空状态。不会再有什么比这更令初音感到恐惧了。
这种欲望结构、依恋关系是病态的吗?当然。但如果我们理解初音的处境,就会发现这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当一个人从一开始就被剥夺了主体性,她便只能从他者那里寻找关于自己的定义。而祥子恰好是那个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给予她这种定义的人,是她在虚无之海中唯一能抓住的浮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初音在整部作品中始终处于一种被动、依附的状态,不是她不想独立,而是她根本不知道「独立的自己」是什么样子。她从未拥有过一个稳定的自我,她的自我感完全依赖于祥子的在场和认可。
然而,即便是这样的梦想都是一种奢望,也正因如此它才能成为「梦想」。初音深知,以她私生女的身份其实从来没资格接近祥子,祥子背后的家族在最终一定会禁止她与祥子继续接触,甚至她都不知道祥子在真相大白后会不会对这样的自己心生厌恶。而对此她却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眼见着自己唯一生存的锚点被强行剥夺,离自己越来越远。自己的人生宛如一场大梦,而梦总有醒来的时刻。所以当初音说出这个梦想时,她其实是怀着这样的心境:我知道这只是虚无缥缈、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但即便如此,这依然是我唯一的、也是全部的愿望。
此刻的初音就像站在悬崖边缘的人,明知前方是深渊,还是选择向前伸出了手——不是因为相信能抓住什么,而是因为除了伸手以外已别无选择。对于一个从未被允许拥有任何东西的人,仅仅只是说出「我想要」就已是最大的反抗。
09:03 - 10:25

一个人的美德可以有很多,怎么这里突然来一句「真诚是一种美德」?今天我们知道,祥子父亲的真诚却成了老实人被利用的最大弱点——好人就得让人拿枪指着。
所以即使今天父亲沦落成这般模样,祥子也并不记恨自己的父亲,她仍然记得父亲曾经温柔、正直的样子。我们都知道一个集团 168 亿日元的损失怎么可能是由一个人的失误造成的,清告只不过是作为一个赘婿、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外来者、一个「真诚」的老实人来担当这个替罪羊罢了。清告大概从未想过为家庭努力奋斗、真诚正直的自己会成为一场精心设计的局中人。或许就是因为他太过真诚,才会在不知不觉间成为替家族挡下损失的挡箭牌。驱逐出家族的决定来得如此迅速,丝毫不给他辩解的机会,仿佛早有准备、等着这一天的到来。妻子的突然离世都不曾打倒坚强的清告,可再叠加上这种级别的打击,又有谁还能顶得住呢?

11:28 - 11:48

祥子确实是个坚强的孩子,继承了她父亲的坚强。可这里的「坚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她必须找到某种方式来填补母亲离世后留下的巨大空洞。对于失去重要客体的人来说,最常见的反应就是寻找一个新的客体来填补这个位置——CRYCHIC 就是祥子为自己找到的替代物。看过 Morfonica 的演出后当场拉上睦组乐队,随后又一步步拉来灯、爽世和立希,这一系列行动背后其实是一种对秩序重建的渴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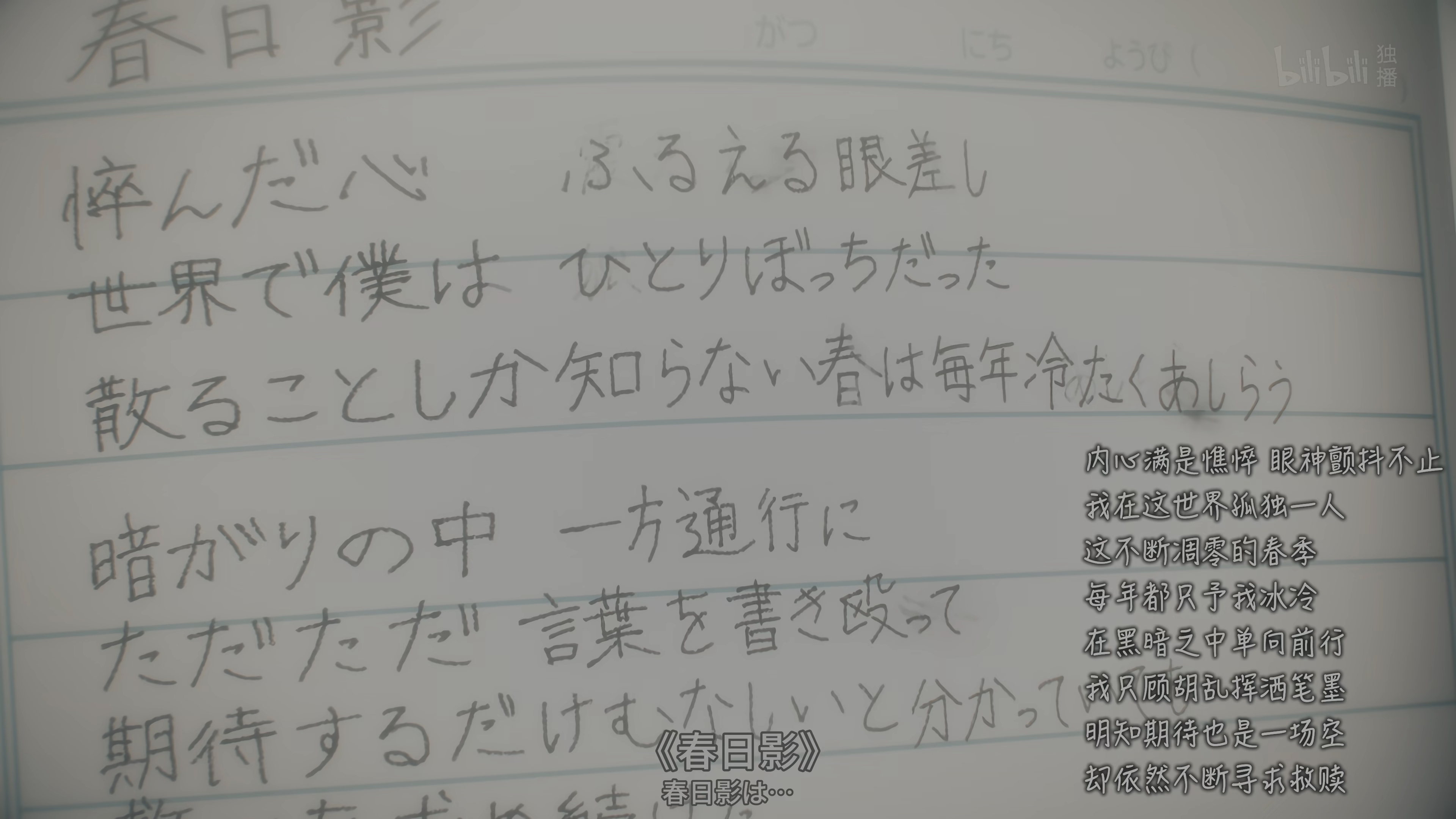
也因此,CRYCHIC 对祥子来说从一开始就不只是玩音乐那么简单,它更像是一个容器,承载着她对稳定、秩序、归属的全部渴望。她积极开导灯、让灯第一次感受到阳光下的温暖,为「春日影」的歌词落泪、认为这是属于大家的歌曲——这些行为背后是祥子在乐队中寻找的某种确定性:只要大家在一起,只要这个团体还存在,她就能确认自己不是孤身一人、确认自己仍然有能力守护些什么。母亲已经无法挽回,但至少她还能守护这支乐队,至少她还能让大家凝聚在一起。
但 CRYCHIC 最终也还是解散了。
「明知期待也是一场空,却依然不断寻找救赎。」这句歌词也同样描绘了祥子的处境。
12:16 - 12:23

天旋地转的运镜是对「KiLLKiSS」的呼应。父亲的离去使祥子再次失去了「重力」,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秩序、稳定的参照系。
12:42

祥子祖父也很无奈,逐出祥子父亲也未必是他的决定,即使是明面上的家主也不能左右整个丰川集团。在真正的资本权力面前,定治也不过是个执行者。
这份无奈其实也是权力结构的一个冰冷的侧写。清告的悲剧不完全是源自某个恶人的阴谋,而是一整套资本逻辑的自然运作。并不需要有人刻意陷害,系统自己就会筛选出那个「运气最差的人」,将其斩杀。当祥子面对祖父时,她甚至找不到一个可以去怨恨的具体对象——因为祖父也只是棋子,只是这个庞大机器上的一个零件。这就是官僚体制的运作方式:每个人都在做自己份内的事,每个环节都有明确的职责和流程,每个决策都可以找到相应的规章制度作为依据。董事会投票、审计报告、法务意见、人事决议——一切都合法合规,一切都按照既定程序进行。但当所有这些「份内的事」组合在一起时,最终的结果却可以碾碎一个活人、摧毁一个家庭。并且最终没有人需要为这个结果负责,因为每个人都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
这种现象不禁令人联想起阿伦特的「平庸之恶」。
「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 是政治哲学家汉娜 · 阿伦特 (Hannah Arendt) 在 1963 年出版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中提出的概念。这本书是阿伦特在 1961 年以《纽约客》特派记者身份前往耶路撒冷旁听纳粹战犯阿道夫 · 艾希曼 (Adolf Eichmann) 审判后写成的。
艾希曼是纳粹德国负责执行「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直接参与了导致数百万犹太人死亡的大屠杀。战后他逃往阿根廷,1960 年被以色列情报机关摩萨德抓获并押送至耶路撒冷接受审判,1962 年被判处死刑并执行。
然而,当阿伦特在法庭上见到艾希曼本人时,她震惊地发现这个策划和执行了如此滔天罪行的人,并不是她预想中那种穷凶极恶的恶魔或变态狂。相反,艾希曼只是一个平庸、普通、甚至有些滑稽的中年男子。在法庭上,他反复强调自己只是「执行命令」「完成工作」「履行职责」,他没有个人仇恨,也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因为他只是在「做份内的事」。
阿伦特由此提出了「平庸之恶」的概念:最可怕的恶往往不是由那些穷凶极恶、丧心病狂的恶魔实施的,而是由那些平庸无奇、毫无思考能力、只是机械地服从命令和执行职责的普通人实施的。这些人不需要有仇恨,不需要有恶意,甚至不需要有任何强烈的情感。他们只需要放弃独立思考,将自己融入官僚体制的齿轮中,按照规章制度办事,就可以成为大规模暴行的执行者。
这种「恶」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不需要任何邪恶的动机,只需要对体制的服从和对思考的放弃。当每个人都只是「做好自己的工作」——有人负责登记名单,有人负责安排火车时刻表,有人负责管理集中营,有人负责操作毒气室——最终的结果就是数百万人的死亡。但没有人觉得自己是凶手,因为每个人都只是在「履行职责」。
阿伦特的这一概念揭示了现代官僚体制的一个核心悖论:一个由「守法公民」组成的、运转良好的、合法合规的系统,最终可能成为最高效的杀人机器。因为在这个系统中,责任被无限分散,每个人都只对自己的环节负责,而没有人对整体负责。当罪行被分解为无数个「正常的工作流程」时,罪恶感也就随之消解了。
在资本主义社会,一切都服从于效率、计算和利益最大化,而人本身的价值、尊严、情感被彻底排除在外。当做出这个决定时,没有人需要关心清告怎么想、祥子以后的人生会怎样。更可怕的在于这个社会消解了一切反抗的可能性,因为系统本身是「理性」、「高效」的,反而考虑人的情感才变得「不理性」、「不高效」。祥子可以选择不要家族的财产、选择到小破公寓陪伴自己的父亲,但这些选择其实改变不了任何结构性的东西。当定治说「你根本就不知道丰川家的黑暗」时,他所指的其实正是这一整套系统,而这种结构性的压迫是祥子这样的个体根本无力对抗的。
15:03

同样的话语,不同的心境。
在之前的那一幕,妻子刚刚去世,清告作为父亲必须站起来,必须给女儿一个支撑。那句「爸爸会努力的」是一句承诺,也是一种自我催眠——只要说出来,只要让女儿相信,他自己也就能相信。那是一个父亲在悲痛中强行建立起来的秩序,是他告诉自己「我还能做些什么」的方式。然而如今这句话从酒精麻痹下的嘴中说出时,却已是别一番滋味。
酒精的作用不仅仅是麻痹痛苦,更重要的是它暂时解除了意识的审查机制,让那些被压抑在潜意识深处的东西浮现出来。弗洛伊德认为,醉酒状态下人会回到更原始的心理层面,超我的控制被削弱,被压抑的欲望和恐惧会趁机涌现。所以当清告喃喃自语「爸爸会努力的」时,这实际是他的潜意识对自己的诘问:我真的努力了么?我到底在努力什么?
这句曾用来为自己和女儿振作精神的话语,此刻已变成了一个无法兑现的债务,一个不断提醒他失败的咒语。他曾经真的努力过,为了家庭、为了女儿、为了在丰川家站稳脚跟,他努力工作、兢兢业业。但所有这些努力最终换来的却是被当作替罪羊逐出家门,换来的是一间肮脏的公寓和整日的酗酒。妻子的去世他尚且可以承受,因为那或许可以说是「命运」的不可抗力。但这次不同,这次是人为的陷害,是他引以为豪的「真诚」被当作工具利用的结果,他只是成为了那个「不幸运」的代价。此时,「努力」这个词已经失去了意义。清告不是不想努力,而是他已经不知道还能朝哪个方向努力。所有他曾经深信不疑的东西——真诚、勤奋、责任、家庭——全被证明是一场笑话。他已彻底落入绝望的深渊,而那句「爸爸会努力的」此刻就成了一个恐怖的诅咒,在他的脑海中不断回响。
更残酷的是,他说这句话时面对的是自己的女儿。祥子也同样失去了一切——失去了母亲,放弃了丰川家的身份和财产,退出了亲手创建的 CRYCHIC。而这一切在清告看来,归根结底都是因为他自己作为父亲的无能,都是他的错。清告当然知道女儿为了他放弃了什么,也因此这份对女儿的愧疚比任何外部的指控都更加沉重。此刻的女儿对他越好,这份愧疚就越是令他崩溃、无地自容。此时他内心的潜台词是:对不起,爸爸对不起你,爸爸本来应该能保护你的……
但爸爸失败了。
15:27 - 16:02

伏笔回收,解释了上一季「为什么祥子突然退出 CRYCHIC」这个核心谜团。
对现在的祥子来说,问题已不在于「是否要退出」——她如何可能放弃现如今唯一的亲人,独自岁月静好——而是「要如何离开」。要坦白一切吗?只要说出真相,乐队的伙伴们都会围上来,同情她的处境,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让她不要一个人自己扛,「我们都在」。但这恰恰是祥子无法接受的。她不需要怜悯,更不希望 CRYCHIC 变成一个救济落魄大小姐的互助会。一旦真相大白,大家一定会为了照顾祥子的自尊而每天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本来单纯的音乐梦想也会蒙上一层阴影。那样的 CRYCHIC 在祥子看来也已与死无异,她也不希望自己的处境连累无辜的同伴、自己成为大家的负担。
所以她选择了一个最残忍也最决绝的方式:不解释、不道歉、不留任何商量的余地,冷血地宣布退出。在同伴面前,她必须表现得冷漠、不近人情,仿佛这个决定对她来说轻而易举,仿佛她根本不在乎 CRYCHIC,仿佛过去那些一起练习、一起演出的日子都不值一提。只有这样,同伴们才会恨她而不是同情她,才会觉得「是祥子抛弃了我们」,斩断一切可能产生的怜悯与愧疚,让她们能毫无负担地将她切割、继续前行。

这是一种近乎自毁的温柔。她在排练室里表现得越是无情,在雨中哭得越是狼狈,一切强行压抑的悲伤、不舍、痛苦、绝望都在雨中爆发。她成功骗过了所有人,却唯独骗不过自己。这种「宁我负人」的决绝,与她那个默默扛下所有罪名被逐出家门、要求女儿「从我眼前消失」的父亲如出一辙。他们都太骄傲,骄傲到宁可被误解、被痛恨,也不愿在他人的怜悯中苟延残喘;他们又太笨拙,笨拙到以为只要自己切断了联系,独自承受一切,就能保护那些重要的人不受伤害。
但这种坚强的代价是什么?是彻底的孤独、无人理解的痛苦。清告在女儿眼中成了整日酗酒的废人、祥子在同伴眼中成了突然背叛的恶人,他们都为了保护他人选择了牺牲自己,但这份孤独也会成为压垮他们的重量。
17:26

圣 · 爱音在这部沉重的作品里确实起到了活跃气氛的作用。MyGO 的小打小闹在 Mujica 全员的创伤症状面前就显得无比快乐温馨。
17:32 - 18:22

我们知道祥子这里是想安慰父亲,希望父亲能振作起来,但很遗憾这两个关键词恰好就触发了清告的雷点:「母亲」、「美德(真诚)」,哪壶不开提哪壶。这里也算是与前文的照应,对「真诚」的反复强调是为了明示 168 亿诈骗案和清告其实没什么关系。

这里就是前面提到的,祥子退出 CRYCHIC 的镜像。清告希望女儿能没有心理负担地将自己切割,留在丰川家会有更好的前程。宁可留下一世骂名,也希望至少女儿能够获得幸福。等一切安排妥当,自己也就能安心地去自杀了。这是他给女儿的最后一份礼物,也是他作为父亲唯一还能做的事。
可惜导演没类似地安排祥子夺门而出后父亲独自哭泣的镜头,信息不对称导致了观众的误解。虽然我感觉这里清告扔完啤酒罐后态度的突然转变、痛苦的哭腔与颤抖的身体已经足够表达他此时内心的复杂情感了——那是一个溺水的人在最后一刻拼命把女儿推向岸边。
18:25 - 18:56


前一秒,祥子还在睦面前泣不成声、哭诉自己的心情无人理解,但下一秒睦一句「武道馆没问题吗」,祥子就瞬间切换成了「黑祥」形态:「能有什么问题?你以为我是为了什么而努力到现在的?」
这种看似突兀的切换是一种典型的、条件反射式的心理防御机制。刚才我们分析了清告如何用「给我消失」将女儿推开、以伪装的暴戾掩盖内心的绝望,此刻的祥子也是如出一辙:将脆弱封入壳中,尝试成为一个只剩目标、不再有情感的容器。这到底是怎样一种心理机制?
唐纳德 · 温尼科特 (Donald Winnicott) 是英国精神分析学家,客体关系学派的核心人物。他在临床实践中观察到一个现象:有些患者表面上适应能力极强、社交得体甚至事业有成,内心却感到空虚、不真实,仿佛自己一直在「演戏」。由此他提出了「真实自体」(True Self) 与「虚假自体」(False Self) 的理论。
温尼科特认为,婴儿最初的心理状态是一种全能感——饿了就哭、开心就笑,所有的情感和需求都是直接的、未经修饰的,这就是真实自体的原初形态。如果养育者能够「足够好地」回应婴儿的需求——不必完美,只需大致到位——婴儿就能在安全的环境中逐步发展出一个健康的人格,既能表达自我也能适应外界。
但如果养育环境出了问题——养育者的回应不稳定,或外部环境过早地要求婴儿去适应他人的需求——婴儿就被迫面临一个选择:放弃自己的真实需求,转而迎合环境的期待。这时一个虚假自体就开始形成。
虚假自体的核心功能是保护。它像一层盔甲包裹住脆弱的真实自体,向外呈现出一个「该有的」「合适的」形象。虚假自体可以非常成功,它能让人在社会中显得坚强、优秀、令人信赖,但代价是真实的情感和需求被深深压抑,主体越来越感到空虚和不真实。虚假自体越成功、越牢固,真实自体就越萎缩。
温尼科特尤其指出一种危险的情况:当真实自体遭受了严重创伤时,虚假自体会被大幅强化,几乎完全取代真实自体的位置。此时主体的一切行为都是在「表演」——他们清楚什么时候该笑、该悲伤、该坚强,但这些都不是真正的情感反应,而是虚假自体根据环境需求做出的「正确回应」。从外部看,他们坚不可摧;从内部看,真正的他们早已缺席。
此刻的祥子正是在我们眼前完成了一次虚假自体的加固——说是「加固」而非「建构」,因为这恐怕已不是她第一次启动这套机制了。前一秒泣不成声的她是真实自体的短暂泄露,后一秒冷硬如铁的她则是虚假自体重新接管了控制权。「能有什么问题?」与其说是在回答睦,不如说是在压抑自己的脆弱与恐惧。父亲将真诚传给了祥子,却也将这种以压抑真实自我为代价的「坚强」一并传给了她。

「除了 Ave Mujica,我已经一无所有了。」——匮乏在说出口的瞬间又被缝合,只要 Ave Mujica 尚在,这个空洞就暂时不必直面。一个已经一无所有的人将全部生存意义押在唯一剩余的客体上,这个客体就不再只是一支乐队了——它已成为主体崩解前的最后防线,唯一还能确认主体自身存在的锚点。祥子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约翰 · 鲍尔比 (John Bowlby) 是英国精神分析学家,「依恋理论」(Attachment Theory) 的创始人。他的工作彻底改变了发展心理学对亲子关系和人格形成的理解。
鲍尔比的核心观点是:人类天生具有与特定个体(通常是主要照护者)形成持久情感纽带的倾向。这种纽带被称为「依恋」(Attachment),它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进化赋予的生存机制。在与照护者的早期互动中,个体会逐渐形成所谓的「内部工作模型」——一组关于「自己是否值得被爱」和「他人是否值得信赖」的核心信念。这个模型一旦形成,就会深刻影响此后所有的人际关系。
鲍尔比的后继者玛丽 · 安斯沃思 (Mary Ainsworth) 通过实证研究将依恋模式划分为四种类型:
- 安全型 (Secure):照护者的回应一致且敏感。个体相信自己值得被爱,也信任他人,能自如地建立亲密关系。
- 焦虑型 (Anxious-Preoccupied):照护者的回应时有时无。个体渴望极度亲密,却永远担心被抛弃,表现为过度依赖、反复寻求确认。
- 回避型 (Dismissive-Avoidant):照护者持续冷漠或拒绝。个体学会了「不需要任何人」,用独立和自给自足作为防御。表面强大,内心孤立。
- 恐惧-回避型 (Fearful-Avoidant):照护者的行为不可预测,有时温暖有时造成伤害。个体同时渴望亲密又恐惧亲密,在关系中反复无常——时而热烈投入、时而突然抽身。这是最不稳定的依恋类型。
鲍尔比还在其三部曲著作——《依恋》《分离》《丧失》中详细研究了丧失重要依恋对象后的心理反应过程。他描述了三个阶段:抗议(拒绝接受,愤怒和寻找)→ 绝望(接受现实,陷入悲伤)→ 超脱(表面上已「走出来」,实际上是将情感需求封印起来)。
「超脱」阶段尤其值得注意。处于这个阶段的人看似已经痊愈——不再哭泣、不再提起逝去的人、甚至显得比之前更加坚强和独立——但这只是一种防御性的冷漠。真正的悲伤并未被消化,而是被隔离在了意识之外。更关键的是,如果丧失反复发生——一次又一次地失去依恋对象——这种防御就会不断强化,最终固化为一种稳定的人格特征:不再期待,不再信任,不再投入。因为每一次投入都曾以丧失告终。
回顾祥子走到这一刻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清晰连续的依恋对象丧失链:母亲去世、离开家族、CRYCHIC 解散、与父亲决裂。每一次丧失都是在不断锤打同一个信念——我所依赖的一切终究都会失去。
祥子的依恋模式呈现出典型的恐惧-回避特征。她既渴望亲密(组建 CRYCHIC 把所有人聚在一起、信赖睦、接纳初华),又极度恐惧被抛弃(不做任何解释地退出 CRYCHIC)。在「超脱」的防御被反复加固之后,她学会了不再悲伤、不再依赖任何人——「唯一能相信的只有自己」。这就是虚假自体与不安全依恋在同一个人身上交汇的结果:虚假自体提供外壳,不安全依恋决定了这层外壳内部的运作逻辑。
在所有依恋对象都已丧失、只剩 Ave Mujica 的此刻,全部的恐惧就集中到了一个点上:绝不能再失去,而祥子对恐惧的表达方式就是控制。这种结构内含着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恐惧催生控制,控制制造压迫,压迫酝酿反弹,而反弹最终指向的却恰恰是她最恐惧的那个结局。
20:58 - 23: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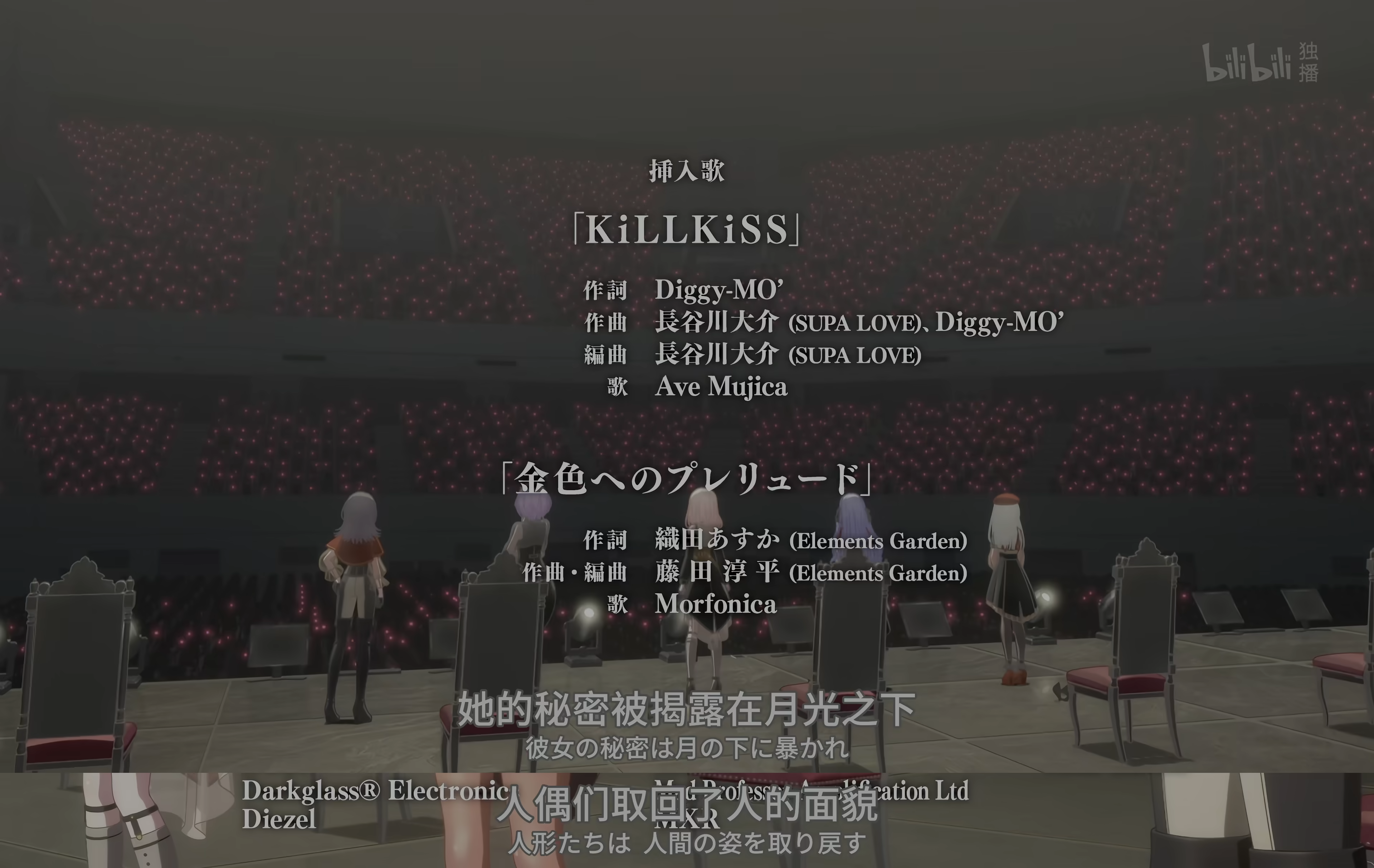
若麦终于动手了,她先是摘下自己的面具,然后强行揭下睦和海铃的面具,最后是祥子和初华在观众的哗然中被迫跟随。若麦的行为动机在 06:05 节已经分析过了,是源自这个快餐时代的注意力经济。面具在她眼中的唯一功能就是被揭下的时刻所制造的爆点,而在武道馆这种规模的舞台上无疑是流量收割的最佳时机,若麦一直等待的就是这个舞台。
可是,这个行为对其他几位成员又意味着什么?
欧文 · 戈夫曼 (Erving Goffman) 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社会学家之一。他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中提出了「拟剧理论」(Dramaturgical Theory),用戏剧的隐喻来分析社会交往的结构。
戈夫曼认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就像舞台上的演员,持续进行着「印象管理」。社会空间由此被划分为两个区域:
- 前台 (Front Stage):面对观众的区域。人们在前台按照社会期望管理自己的外在形象、言行举止,呈现出一个经过修饰的「社会面孔」。
- 后台 (Back Stage):远离观众的区域。人们在后台可以卸下伪装、展露疲惫、练习台词、处理不宜公开的事务。后台是恢复与准备的空间,也是真实自我得以暂时栖身的空间。
这种前台 / 后台的区分不仅仅是空间上的划分,更是一种社会契约——它保护了个人的自主性。你有权选择何时、以何种方式、向谁展露自己。后台的存在意味着你可以在准备好之前不必面对观众的审视,你的脆弱、矛盾、混乱不必成为公共景观。
戈夫曼由此揭示了一个常被忽视的暴力形式:强行将他人的后台暴露于前台。当一个人的后台被未经许可地公开——不论出于善意还是恶意——都构成对其自主性的侵犯。这种侵犯剥夺了主体管理自我呈现的能力,强迫他们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面对他者的目光。
有了拟剧理论的视角,面具在这部作品中的功能就不再只是遮挡身份,而同时也是前台 / 后台之间的物理边界,允许角色在舞台上演出时仍保有一个不被穿透的私人空间。
对不同角色来说,面具的意义也彼此不同。对若麦而言,面具是注意力经济的障碍。在她的逻辑中,后台就不应该存在,因为一切未被看见的东西都是流量的损失。对祥子而言,面具是虚假自体的物质外化。回顾 18:25 节温尼科特的分析:祥子的虚假自体像一层盔甲包裹住脆弱的真实自体,对外呈现出一个坚强、可控的形象。面具就是这层盔甲的可见形式,它保护的正是虚假自体赖以运作的后台空间,一个可以暂时不必「坚强」的空间。而摘下面具就等于强行拆除虚假自体的外壳,将祥子濒临崩溃的内心暴露在上万观众的视线之下。对睦而言,面具或许是五人之中最不可或缺的。05:11 节我们分析过,睦既不愿说出那些自己不相信的空洞话语,又恐惧说出真心话会再次像 CRYCHIC 时那样摧毁一切。面具可以让睦暂时不必以「若叶睦」的身份面对镜头和话筒,不需要扮演「知名演员之女」的角色。而面具一旦被摘下,这层屏障也就不复存在。接下来她将迎来媒体对其家庭背景的全面曝光、如潮水般涌来的采访与舆论压力,这些都将使睦的精神状态进一步恶化。
所以若麦在舞台上的行为,用戈夫曼的术语来说,就是一次对所有成员后台的强制曝光。正如我们在 18:25 节提到的那个自我实现的预言,祥子越是害怕什么,她的行动越会实际上导致什么的发生。场面失控,一切都开始急转直下。
「玫瑰之下」
01:10 节我们说过,月光容许秘密的存在、不要求彻底的暴露。而此刻发生的恰恰是月光秩序的破裂:聚光灯取代了月光,后台翻转为前台,秘密逐渐从「玫瑰之下」被拖入公众视野之中。不过月光保护的那些真正的秘密此刻仍深埋在「玫瑰之下」,表面的揭露反而强化了深层的遮蔽,正如海德格尔所言:每一次「解蔽」都必然伴随着新的「遮蔽」。聚光灯照亮了面孔,却让面孔之下沉入更深的黑暗。
05:01 节我们说过,这个故事将要展示的是「如何坠落」。武道馆是传统叙事的终点,Ave Mujica 却以此为起点。如今,作为符号象征的面具业已碎裂,这场崩溃也就此拉开序幕——

ねぇ あからさまね 醜い終局に すべてが変わってゆく
そう このまま 壊れて
(未完待续)